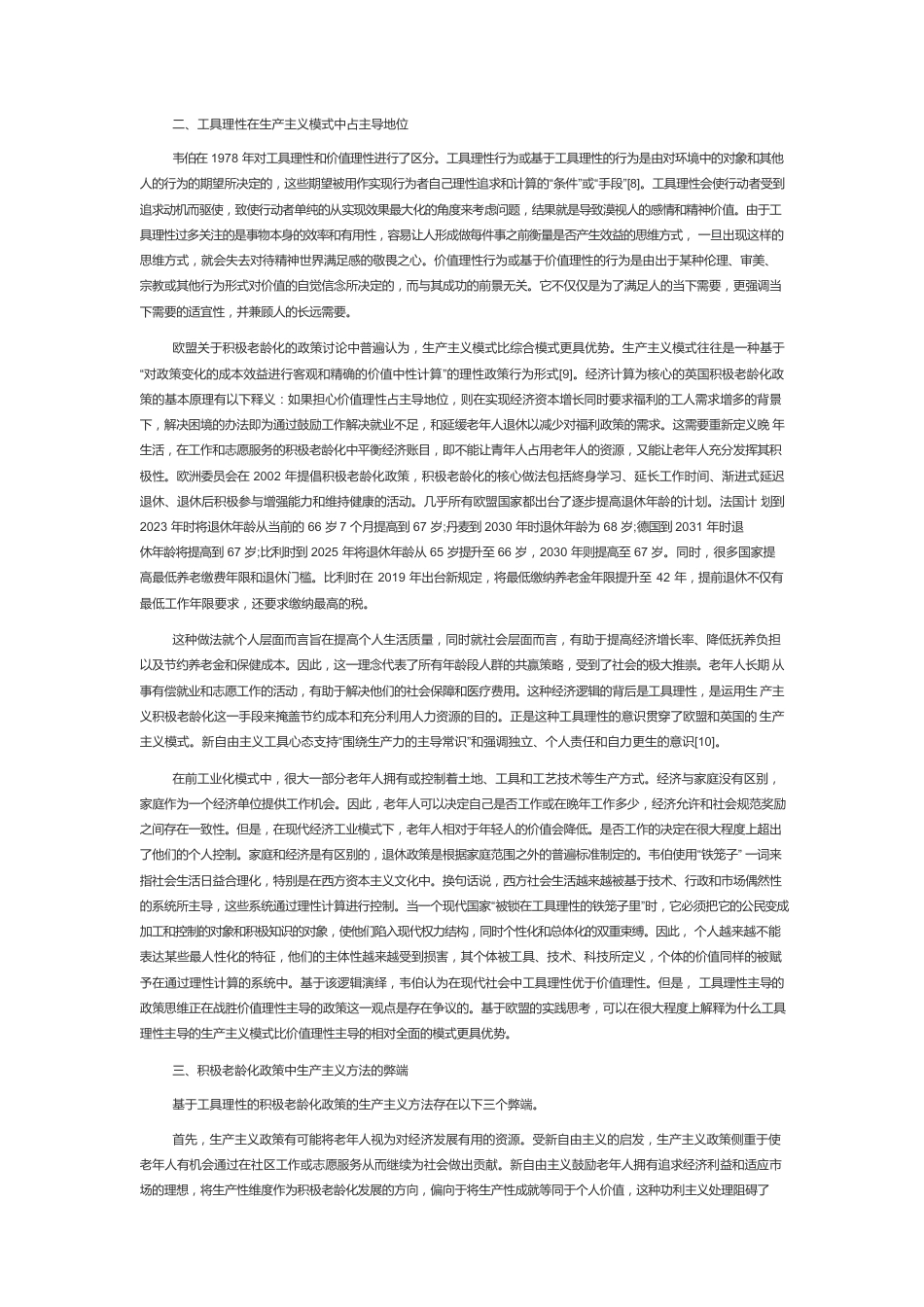老龄化政策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进行统筹谋划、系统施策。积极老龄化已经成为以幸福晚年生活为特征的政策概念和政策价值导向,并被世界各地广泛接受,然而学术界对积极老龄化的理论内涵和政策价值导向存在争议。关于积极老龄化已经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政策议题,一是强调全面处理老龄化的相关问题,注重老年人的方方面面,这一政策价值导向得到了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欧盟委员会的大力倡导与支持;而另一种是偏向强调积极老龄化中的生产主义方法,遵循经济逻辑背后的工具理性,这一类型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在分析西方老龄化政策理念发展变迁的基础上,分析积极老龄化政策的生产主义方法带来的弊端,进而基于我国国情找到平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途径。一、西方老龄化政策理念的发展与变迁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中,西方国家经历了从强调老年人功能障碍、依赖性和被动性的福利导向政策思维转变到强调老年人功能性、自力更生和积极性的福祉导向,这体现了“从福利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转变”的思潮在当代西方国家的老龄化政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从福利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转变”思潮主导下,西方老龄化政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提倡的成功老龄化,1987年世界卫生大会上提出的健康老龄化,2002年联合国第二次老龄大会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是RobertButler于1982年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办的一次老年学会议中提出的。RobertButler认为,关于老年人的“无生产力迷思”是没有根据的,这一论点会导致对老年人生产和创造能力作出悲观结论,如果抛去功能障碍和“社会逆境”的影响,老年人可以富有生产力并积极参与生活[1]。与生产性老龄化相反,成功老龄化这一政策理念作为老年退出社会的对立而产生。区别于病理性变化的“正常老龄化”,Rowe&Kahn进一步将老龄化过程划分为常态老龄化(没有疾病但存在着较高的风险)和成功老龄化(较低的风险和较高的身体功能水平)[2]。实现“成功老龄化”的关键在于把老年时期当作中年人活动的延续和其典型价值观的保留。如果过分强调成功老龄化,老龄化政策关注重点人群会从那些因年龄增长而遭受疾病和残疾的人转向状态好的的老年人群,忽视对弱势和特殊老年群体的关注。此外,成功意味着有赢家和输家,但大多数老年人不愿意因为残疾或健康不佳的生理特征而被贴上不成功的标签。继生产性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之后,1997年6月在丹佛举办的八国集团峰会上提出积极老龄化。2002年,WHO“老龄化与生命历程项目”向第二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提交了《积极老龄化:一个政策框架》的报告,主要从健康、参与和保障三个维度阐释积极老龄化的含义,信息技术使人们能够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实现身体、社会和精神健康方面的潜力,并根据自身的需要、愿望和能力参与社会,同时在他们需要援助时向他们提供充分的保障、安全和照顾[3]。积极老龄化这一观点挑战了老年人以往被贴上的“被动的和依赖的”特征标签,强调了老年群体的自主性和参与性。通过梳理老龄化政策发展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生产性老龄化的理论缺陷,它被一种狭隘的经济或生产主义观点所主导,优先考虑延长工作寿命。传统观点认为老年人是无价值的。生产性老龄化观点则认识到,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可以经常参与在其社会背景下具有社会经济价值的活动。Morgan最先提出老年人的生产性活动包括任何生产物品和提供服务的活动[4]。Butler&Schechter认为生产性是老年人个人或群体从事有偿工作、志愿者活动、支持家庭等活动的能力,以及尽可能独立地维持自己的能力[5]。这些概念被批判为是对一些群体强加消极判断,例如,家庭主妇和没有能力获得体面薪水的孱弱老年人就被“生產性”观点消极化。Moody认为,生产性老龄化包括老年人从事的各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主要分为四类:参与有偿或无偿工作,照顾家人、亲戚和朋友,参加各种志愿者活动,参与终身学习以提高其人力资本和生产力[6]。Kim也提出了四个类别:狭义的生产活动,即参与...